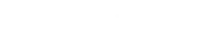而1919年也是巴黎和会召开和五四运动爆发的日子 , 当时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前往巴黎 , 支持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
此后 , 丁文江前往美国 , 为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寻找急缺的古生物学人才 , 辗转联系到正值困境的葛利普 , 双方一拍即合 。
就这样 , 葛利普来到了中国 , 担任北大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 。
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研究和教学都不成体系 , 古生物学方面更是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和成果 。
葛利普的到来 , 使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立即成为国内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学术中心 。
1922年 , 葛利普参与创建了中国地质学会 , 协助创编了《中国古生物志》 , 并撰写了包括《中国古生代珊瑚化石》在内的多篇文献 , 使得中国古生物学在短期内就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 。
由他著述和编制的《中国地层》、《亚洲古地理图》 , 是当时对中国乃至亚洲地质历史最完善的总结 。
对这种种辉煌的成就 , 李四光后来评价葛利普时说道:“我国地质 , 初具雏形 , 提之携之 , 赖公有成 。 ”
除了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 葛利普还竭尽心力培养了中国最初的一批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人才 。
葛利普患有风湿病 , 腿脚不便 , 需要借助拐杖或轮椅才能行动 , 但他总是准时上课 , 风雨无阻 。
他常对学生说:“不要老落在岛国日本的后面” , “在你们的国家里 , 你们是发展这门学科的先锋” , “将来在你们的国家里 , 科学的大厦一定会耸立起来的 。 ”
在他的悉心教导下 , 涌现出包括孙云铸、赵亚曾等许多我国古生物学的专家和人才 。
据统计 ,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有19个年级的学生听过葛利普的课 , 其中诞生了2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 包括11名古生物学的院士 。
不幸的是 , 时代造就了葛利普在中国的成就 , 也宿命般地影响了他的余生 。 七七事变爆发后 , 日军占据了北平 , 日伪方面接管了北大和地质调查所 , 留在北平的葛利普宁愿变卖家产 , 也不接受伪北大教职 。
他鼓励同事和学生前往大后方 , 自己却无力南下 , 与学生道别之际 , 他几番呜咽不能成声 。
1941年 , 他写信给身为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的孙云铸 , 信中说:“我希望我们过去共同从事的事业在你们那里继续兴旺” , “希望我们大家能相会在即将到来的幸福时日” 。
然而 , 他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 。
1941年底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日寇将年逾古稀的葛利普关入东交民巷的集中营 , 身陷囹圄的他 , 仍颤手著述了其遗作:《我们生活的地球:地质历史新解》 。
抗战最终胜利 , 葛利普却因为在集中营饱受折磨而病入膏肓 。 他总是神志不清地问那些前去探望的人:“你是我的学生吗?”1946年 , 葛利普在弟子们的陪伴下去世 。
在弥留之际 , 葛利普多次提出希望能加入中国国籍 , 很可惜 , 那时已经来不及办理了 。
遵照他的遗言 , 其二千余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国地质学会(现存中国地质图书馆) 。 李四光为葛利普书写挽联:“述作最丰 , 伟著共欣传后学;论交至笃 , 同人齐恸失宗师 。 ”
1982年 , 在葛利普参与创建的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之际 , 中国地质学会与北京大学决定 , 将葛利普墓由北大沙滩旧址(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迁入现北大校园内 。
如今 , 矗立在北大西门内的葛利普教授之墓 , 永久地象征着我们对这位中国古生物学之父的崇敬与怀念 。
推荐阅读
- 教师|北大韦神“真实处境”跌下神坛,学生退课,班级人数不到10人
- 大学|大学哪些专业对身高要求?这6类差1cm也报不上,家长和学生要清楚
- 维修|把专业和课堂建在“产业链”上
- |2022国考面试专业专项考情介绍:无领导小组讨论
- 西北大学|普陀这些学校荣获市级荣誉!看看有你的母校吗?
- 大学|金融专业美国硕士留学需要做什么准备?
- 高校|省人社厅、省档案局关于深化档案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四)
- 古生物|北大“六代单传”的专业,一人请假全院停课,毕业照学生自己拍
- 大学生|继专业课后,疑似公共课也阅完了,查分时间会有变动吗
- 考研|这6个考研“冷门”专业,只求“上岸”的考生,可以试一试!